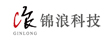导语:德国的能源革命旨在以新型能源取代核能发电与化石燃料。跟随国家地理看可再生能源法的起源故事。
本文经由国家地理中文网暨华夏地理同意转载


德国东部,格赖夫斯瓦尔德附近,工人们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逐步拆除这座苏联时代的核电厂,用钢屑清理带有放射性的面板(上),以便回收旧金属。德国计划在2022年以前关闭境内所有反应炉。

卡尔卡的核反应炉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熔毁事故发生前刚刚完工——后来从未投入使用。现在它变成了游乐园,游人可以在原本是冷却塔的巨筒里飞旋游览。对核能的恐惧刺激了德国的能源转型进程。

距德国大陆50公里、北海海面上空约90米处,一名工程师在检修由丹麦DONG能源集团运营的风电涡轮机。德国在北海、波罗的海建成及在建的风力发电场已有19 处。
汉堡民众知道盟军的炸弹就要来了,所以战俘和强征的劳工必须在半年内建起巨大的高射炮碉堡。1943年7月,碉堡完工。这是一座没有窗户的钢筋混凝土立方体,墙厚2米,房顶更厚,像中世纪城堡般矗立在易北河附近某公园之侧。炮口从四个炮塔伸出,准备向空中的盟军轰炸机扫射,此外纳粹党人还保证,数以万计的市民可以在坚不可摧的墙后安全避难。
碉堡落成后刚过了几个星期,英国轰炸机于夜间从北海袭来,向汉堡市中心圣尼古拉教堂的尖塔飞近。它们撒下大团大团的条形金属箔来迷惑德国人的雷达和高射炮,然后对准密集的居民区投弹,燃起冲天烈焰。火助风势,摧毁了半个汉堡市,死者逾3万4000人,炽热的狂风甚至能把人吹进火场。教堂的钟疯了一般轰鸣。
圣尼古拉的尖塔居然幸存下来,今日成了一道纪念景观,提醒人们不忘当年纳粹酿成的巨祸。那座高射炮碉堡也是纪念物,但如今却被赋予新的意义:从德国羞耻历史的见证,被改造成了光明未来的象征。
碉堡的中央空间内——在当年人们躲避轰炸的地方,一座有六层楼高、容量200万升的热水箱向周边市区的约800户人家输送供暖及生活热水。烧水的热能来自污水处理厂产生的燃气、附近一家工厂的废热、以及碉堡顶上覆盖的太阳能板,连后者的支架都是用从旧炮塔里拆出来的废铁制成。碉堡还利用阳光发电:南面外墙上架设的光伏板接入电网,产能足可供一千户人家使用。北面的胸墙曾是当年炮手看着城里燃起大火的地方,现在成了一处露天咖啡吧,供游人观赏面貌一新的天际线——那里点缀着17架风力发电涡轮。
德国正在引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并创造了energiewende这个词来称呼它,意为“能源转型”。科学家们说,若要使地球免遭气候灾难,所有的国家迟早都必须完成这样一场能源革命。其中,德国是当世工业大国中的领导者。去年,其27%的电力来自风、阳光等可再生能源,这个份额是十年前的三倍,是今日美国的两倍以上。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熔毁事故促使德国加速转变,更使得总理默克尔宣布,德国将于2022年以前关闭全部17座核电厂。迄今已关闭9座,而可再生能源绰绰有余地补上了产能缺口。

亚斯蒙德国家公园位于波罗的海,白垩峭壁几世纪来一直吸引着游客。这样的山毛榉树林一度覆盖着德国全境。浪漫主义时期的民间故事中说,森林造就了德国人热爱自然的民族性格;德国正是在如此性格的推动下走进了清洁能源革命。护林员里科·马尔克曼讲解道,1920 年代曾有一家采石场打算进入这里作业,“民众没有容它乱来”。
然而德国对世界的真正重要性却在于:它也许能带领世界甩掉化石燃料。科学家说,我们必须赶在本世纪内把令地球变暖的碳排放基本截停。德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已制定了一套极具进取性的减排目标——以1990年的排放量为基准,至2020年降低40%,至2050年至少降低80%。
现在看来,这些目标最终能否达成还很难说。德国的能源革命是起于草根的:可再生能源领域一半的投资是募自个体公民与当地公民组织。但对这场革命始料未及的传统公共事业公司却在对默克尔政府施压,要求放缓转型速度。德国燃煤发电的份额仍远远高于可再生能源发电,运输、供暖领域的转型更不成熟,而后两者加起来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发电厂还多。

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但德国对污染性最强的褐煤的使用量没有下降。在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掌控的南韦尔措矿区,一台台世界最大的机械在这条14米厚的煤层中挖掘,年产2000万吨。这样的景象还会持续多久呢?“我希望很久,”年轻的工程师扬·多曼说,“我们有足够的褐煤。”

设在丹麦的一座“西门子”工厂里,工人在为一片风电涡轮桨叶进行喷漆前的准备工作。这片桨叶是以玻璃纤维和树脂制成的中空结构,75米的长度几乎可与最大型喷气机的翼展相比。北海中的一架风电涡轮就能为6000户德国家庭供电。
德国政客有时会把能源转型与美国“阿波罗号”登月相比,但完成登月壮举用了不到十年,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参与只限于在电视上看看报道。能源转型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将牵涉每一个德国人。目前该国人口的近2%,超过150万之众,在向公共电网出售自家生产的绿色电力。“这是要尽一代人之力推动的工程。它将持续到2040年或2050年,而且过程艰难。”在柏林的阿戈拉能源转型智库任职的格尔德·罗森克朗茨说,“它正在令个人消费者的电费升高,尽管如此,如果你在普查中问德国人:你愿意接受能源转型吗? 90%的人都会说愿意。”
为什么呢?今年春天我怀着这样的疑问在德国旅行。为什么世界能源的未来先显露于这个国家,这片70年前饱尝轰炸的焦土?这样的未来能通行全球吗?
德意志民族有一个起源传说:其子民是来自幽暗而无路可通的密林深处。这说法可追溯至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他在书中描述过杀得罗马军团一败涂地的日耳曼人,这段远祖旧事被19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所美化。民族志学者阿尔布雷克特·莱曼指出,在20世纪的动荡激变之中,这个起源传说仍是德意志身份认同的稳固源头。森林成了德国人修复受伤灵魂的场所,这样的习惯预先养成了他们关心环境的性格。
所以在1970年代晚期,当戕害德国森林的酸雨被归咎于化石燃料废气排放时,全国上下掀起了舆论怒潮。1973年,OPEC对本土油气资源很少的德国实行石油禁运,已经使德国人开始思考能源问题,而森林之死愈发让他们积极寻求出路。
当时,政府和公共事业公司正在力推核电——但遭到许多民众抵制。这对德国人来说是种新气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里,满目疮痍的国家在等待重建,人们都没什么心思去质疑权威和历史。但到了1970年代,重建工作完成,新一代人开始质疑掀起战争又输掉战争的父辈。“二战导致后来的人们有某种程度的叛逆心理,”五十多岁的德国男子约瑟夫·佩施告诉我,“面对权威不会盲目地接受。”
佩施正坐在弗赖堡城外黑林山的一家山顶餐吧里。在稍高一点的山坡空地上伫立着两架近百米高的风电涡轮机,它们是由佩施招募521名市民投资入股而建成——不过我们还没谈到涡轮机的事。在座的还有一位名叫迪特尔·赛弗里德的工程师,我们正聊到距此地30公里外莱茵河畔维尔村附近一个遭抵制而流产的核电项目。
州政府本来坚称兴建核电厂势在必行,否则弗赖堡的灯火就会断电。但从1975年开始,当地农民、学生占领了施工地。抗议活动持续了近十年,直到他们逼得政府放弃计划。核电建设被截停,在德国是第一次。
灯火当然并未熄灭,而弗赖堡发展成一座太阳能城市。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院的弗赖堡分院是太阳能领域的世界前沿,其“太阳社区”由曾经参加维尔村抗议活动的当地建筑师罗尔夫·迪施设计,里面的50栋房子全部配有发电装置,而且输出大于自身消耗。“维尔抗议是起始点。”赛弗里德说。1980年,赛弗里德参与创建的一家研究所发表了题为《能源转型》的研究报告,为多年后发动的绿色能源运动埋下伏笔。
这场运动并非一战功成,但对核电的抵制——而且还是在世人尚未关注气候变化的时代——显然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来到德国时,心里想着德国人真傻,竟然舍弃一种零碳排放的重要能源:福岛事故前该国有四分之一的电力是核电。我离开时,心里想的是,假如德国人没有反核能情绪,也就根本不会有能源转型运动——与对缓慢升高的气温与海平面的恐惧相比,对反应炉熔毁的恐惧是一种远为有力、直接的动因。
比如把自家房子打造成圆柱形、像向日葵般追着太阳旋转的迪施。比如柏林的罗森克朗茨,1980年他曾连续几个月丢下在物理学研究生院的学业,跑去占领一处规划中的核废料填埋场地。比如露易丝·诺伊曼-科泽尔,时隔20年她又去占领过同一块场地,而如今正在带领一个公民组织收购柏林电网。还有文德林·艾因西德勒,这位巴伐利亚奶农帮助自己的村子焕发出巨大的绿色生命力。
所有这些人都对我说,德国必须同时舍弃核能和化石燃料。“你不能引狼入室来赶走老虎。”知名绿党政客汉斯-约瑟夫·费尔解释道,“两者都留不得。”柏林应用科技大学能源专家福尔克尔·夸施宁的说法则是:“核能影响的是我本人,气候变化影响的是我的孩子,区别不过如此。”
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反核能情绪在德国造成的局面远比其他地方轰烈——比如莱茵河对岸的法国,至今仍从核能中获取四分之三的电力——答案还是要回头从二战中寻找。大战之后,德国被一分为二,成了当世两个核力量超级大国对峙的前线。20世纪70、80年代的示威者抗议的不仅是核反应炉,还有在西德部署美国核导弹的计划,对他们来说这两者似乎是一码事。绿党于1980年成立时,把和平主义与反核能都作为它的宗旨。
1983年,首批绿党议员进驻德国国会,开始把绿色理念注入政治主流。1986年苏联切诺贝利反应炉爆炸时,德国两大党派之一、左倾的社会民主党也转而支持反核运动。虽然切尔诺贝利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它的放射性云团却从德国上空经过,当局告诫民众不要让孩子外出。佩施说,他们至今不能放心食用黑林山的蘑菇和野猪肉。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德国能源运动中的分水岭。
但让默克尔总理和她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下定决心、计划在2022年以前关闭所有核反应炉的,却是25年后的福岛事故。此时,可再生能源事业已然大展宏图,汉斯-约瑟夫·费尔于2000年参与创立的一项法律功不可没。

设在莱比锡的这间部分使用风电的厂房里,宝马公司正在打造i3、i8 两种电动车型,车身使用的是碳纤维轻型材料,这在大批量生产线上是首次应用。德国汽车厂商提供多种电动车型,但由于政府缺少奖励机制,本国人很少买。“与美国加州比起来,我们的电动车产业落后太多。”宝马公司的威兰·布吕赫说。

柏林以北50公里,埃伯斯瓦尔德- 菲诺机场的跑道四周是光伏板的海洋。德国所处的纬度与加拿大的拉布拉多地区相同,日照并不强烈,但利用阳光发电的产能却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大多数太阳能板都安装在屋顶上。

1996 年,位于荷兰边境附近、莱茵河上的卡尔卡核电站遗址作为游乐园重新开张——“卡尔卡奇迹乐园”。德国打算在2050 年以前把自己打造成一种新型奇迹乐园:能源用量比以前低一半、而且其中至少80%为可再生能源的工业大国。
德国的法律为太阳能、风电降低生产成本,使它们能在许多领域与化石燃料竞争,此举带动了可再生能源在全世界的兴起。1990年,东西德正式回归一体的那年,全国上下都在为这场历史性的统一大业忙碌,却有一项推动能源转型的法案顺利在国会通过,尽管并没有在公众中造成多大声响。法案只有两页,确立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生产可再生电力的公民有权向国家电网输送,并且公共事业公司须向他们支付“输电费”。多风的北部地区开始纷纷竖起风电涡轮机。
但当时正在哈默尔堡自家屋顶上装光伏板的费尔意识到,这项新法案永远不能带动全国范围的蓬勃发展:它虽让发电的人们可以拿到报酬,额度却不够。1993年,他推动市议会通过一项法规,强制市公共事业公司保证给任何可再生能源生产者一个有利可图的价格。他很快召集了一批当地投资者,协力兴建功率为15千瓦的太阳能电厂——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微不足道,但这个绿色能源联合会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如今这样的组织在德国数以百计。
1998年,费尔乘着一股“绿潮”、凭借自己在哈默尔堡的成功进军国会。绿党与社会民主党结成了执政联盟,费尔则与该党派中提倡太阳能的著名人物赫尔曼 舍尔联手制定一项新法,借此在2000年把哈默尔堡能源转型实验推向全国,并称为此后世界各地竞相模仿的典范。新法保证了20年内的输电报酬,而且出价颇高。
费尔说:“我的基本原则就是,购电的价格应该能让投资者有钱可赚。我们毕竟市场经济中生活,这样做才合逻辑。”在我遇到的德国人中,费尔大约是唯一自称没有对绿色能源之兴起感到意外的,因为那样的兴起正是由他“合逻辑”的法规开启。“它居然能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当时并不相信。”奶农文德林 艾因西得勒说。在他俯瞰阿尔卑斯山的阳光房外,九架风电涡轮在牛棚后方的山脊上懒洋洋地转动。有牛粪的气味飘来。艾因西得勒于1990年代开始单枪匹马搞能源转型,起步时只有一架涡轮和和一个生产甲烷的牛粪发酵罐。他和痛痒身为奶农的的兄弟伊格纳茨以甲烷为燃料,带动一部28千瓦功率的热点联供机组,为他们的农场供热供电。“当时根本没有想赚钱的问题,”艾因西得勒说,“做事都是理想主义。”
但是可再生能源法于2000年生效后,艾因西得勒兄弟发达了。今天他们拥有五个发酵罐,除了来自八座奶牛场的牛粪还能处理玉米秸秆,并把所获得的生态燃气通过管道输给5公里外的维尔德伯茨里德村;那里运作着多部热电联供机组,供暖对象包括所有公共建筑、一座工业园和130户人家。“这是中绝妙的生活方式,而且削减的碳排放量令人难以置信。”当地官员阿诺岑格勒说。
生态燃气、覆盖着许多屋顶的太阳能板再加上更具产能的风电涡轮机,使得维尔德伯尔茨里德生产的电力是其消费量的近五倍。艾因西得勒是这些涡轮机的管理者,之前找投资商的时候几乎一帆风顺。投资第一架涡轮机的有30人,第二架就是94人。“这些风电涡轮是属于他们的。”艾因西得勒说。哪些巨大的螺旋桨气势磅礴,对德国原野风貌的改变有时会引来争议——反对者形象地称之为“芦笋化”。不过艾因西得勒说,当“芦笋”中蕴含人们的经济利益时,他们的态度会改变。
要说服农户和房屋业主在屋顶安装太阳能板,没有什么难度。政府保障的0.5欧元1度电的收购价(2000年新法刚生效时的价格)相当优厚。2012年时绿色发电浪潮的高峰时期,一年内德国安装的光伏板就有7600兆瓦的产能——阳光充足时相当于七座核电站。德国的太阳能板产业迅猛发展,直到被成本更低的中国厂商抢去风头——后者则推动绿色能源风行全球。
费尔的新法还帮助太阳能、风电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它们能在许多领域与化石燃料竞争。迹象之一是:德国给新建大型太阳能发电设施每度电的收购价格已从0.5欧元降到0.1欧元以下。费尔说:“我们在15年里开创了全新的局面,这是可再生能源法的最大成功。”
德国人为这一成功局面所付出的资金不是通过缴税来来征收,而是变成他们电费账单上的一项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今年这项收费是每度电6.17欧分,一般用户每月累计多交大约18欧元——罗森克朗次对我说,这笔费用对有些人来说是种负担,对一般工薪阶层则不成为题。德国经济整体的电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与1991年相比没什么变化。
撰文:罗伯特·孔齐希 Robert Kunzig
摄影:卢卡·洛卡泰利 Luca Locatelli
翻译:王晓波
本文原载于《华夏地理》2015年12月号
华夏地理微信公共号: